
我的下身只剩下了一条内裤,也被他们撕得丝丝缕缕。
我放弃了抵抗,伸手四处乱摸,摸到衣架上的一根铁杆,挥起来就朝他们打去。
铁杆砸在一个男人的脑袋上,那个男人僵住了,身体摇摇晃晃要跌倒,被身边的人扶住了。
我当时完全疯了,嘴里发着尖叫挥起铁杆又打了过去,一连打了好多下。
我的笨表现在各方面,连打架都笨,我的几杆子都瞄准一个位置打,就是那个男人的脑袋,鲜血从他头顶淌下来,流了一脸。
他们扶着那个受伤的男人后退,我仍在打,铁杆长,又打中好几下。
最后一下打在铁杆的端头,似乎力道更大,那人软软地跌倒了,扶都扶不住。
我还在挥舞着铁杆,是突然赶到的警察控制住了我。
警察把那个脑袋出血的男人用担架抬走送去医院了,我和其他人被戴上了手铐。
警察随便从我店里拿了一身男装让我换上,太大了,松松垮垮的。
阿灵来了,她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手里的饭盒脱手掉了地,她向我跑过来,被警察拦住了。
她喊道:“小苇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我也不敢看她,我第一次有了耻辱的感觉。
我流不出眼泪,心底却在汩汩地流着血。
我多么希望我从未认识过阿灵,那样我就可以无视耻辱,无视任何人的眼光。
在刑警队,警察告诉我,大勇是有家的,那个一马当先扇我耳光的胖女人就是他老婆,那个被我打得脑袋出血的男人是他小舅子,其他人也都是他老婆的家人和亲戚。
他老婆每周六日都要带着儿子去娘家住两天。
原来我真的只是个偷鸡摸狗的小三而已,还是个给人临时填补空位的小三。
但警察似乎不相信我不知道大勇有老婆,因为大勇告诉他们,是我主动勾引的他,而且甩不掉,所以才被他老婆发现了。
我争辩:“我不知道他有老婆,全商场的人都不知道他有老婆!”
警察说他们调查过,商场里的很多人都知道大勇有老婆,又说我每周末都要去大勇家里住两天,持续了半年多,说不知道他有老婆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有女人的家和没女人的家应该不难看出来。
可我就是没看出来,我想解释,警察摆摆手说:“你们的这些风花雪月法律管不了,我们羁押你是因为你伤了人。”
我问我会被判多少年,警察说目前还不好说,要等到调查结束后交由法院审理后才能确定,他们只管调查事实,量刑是法院的事。
我倒真希望我能被判得重一点,最好能被判死刑,无期也行。
我是个傻子,和外面的花花世界格格不入,或许在里面能活得其乐无穷。
我在刑警队录完口供就被送进了看守所。
我曾经对阿灵说过,我这辈子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不会坐牢,因为我不犯法,别的事我主宰不了,这个事由我说了算,没想到一语成谶。
警察把我交给了看守所,看守所的管教给我办理了入住手续,我就名正言顺地在看守所安家落户了。
我的十个手指头的指纹和两个手掌的掌纹,以及我穿着蓝马甲站在一块标有身高刻度的牌子前照的正面和侧面的照片就成了我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记。
咣当一声,我和七个同是穿着蓝马甲的神情呆滞的女犯人成了舍友。
看守所的生活简单而规律,倒是比较适合简单而迟钝的我。
我和七个舍友按时起床,不能早起也不能晚起,整理完被褥后开始洗漱。
为了预防犯人自杀或者相互伤害,牙刷很软,也没有把儿,只有个头连着个指套,手指充当把儿。这样刷牙很别扭,需要把整根手指塞进口腔里。
吃饭的饭盒和勺子也是用软塑料做的。
饭菜免费不限量,不过只有瓷实的馒头和散发着泔水味的水煮白菜汤。
有钱的可以报小灶,小灶有菜有肉有米饭,不过很少一点。
阿灵往看守所交了钱,但我没报小灶,我只买了一身睡衣和睡裤。
我的衣服在入监时被查出有金属部件,不能带进监室。
未决犯是不允许探视的,所以阿灵没见到我,只让管教给我捎了一本书进来,是我送她的那本戴望舒的《雨巷》。
她在扉页上写了字: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小苇,加油!”
我每天打坐的时候就捧着这本书看。
我们每天上下午都要打坐一次,八个人成排成行地盘腿坐在大通铺上,或者看书,或者冥想反思,不准起来,不准相互说话,保持坐姿,保持严肃。
但我看不太懂那些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诗句,我只盯着阿灵写在扉页上的这几行字看。
我想阿灵真是高看我了,我能活着已勉为其难,何谈“天降大任”?
从那时起,我开始失眠,倒不是因为我想得太多,而是因为我睡在通铺的正中间,头顶是彻夜不灭的明晃晃的电灯,即使我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到它的亮光。
我们睡觉不能蒙头,还要保持睡姿,摄像头二十四小时无死角监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挨着我睡的是个瘦削的中年女人,大家都叫她吴姐。
她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整天目光痴呆地望着一个地方,但我感到了她对我的敌意,她看我时总是目露凶光。
据舍友们说,吴姐是个女强人,生意做得很大,老公却不务正业,整天花天酒地,还用她赚来的钱包养小三。
吴姐大怒,找到小三痛揍了一顿,下手重了,小三受伤住院,吴姐也因故意伤人被判了四个月的刑期。
未完待续
文/鄂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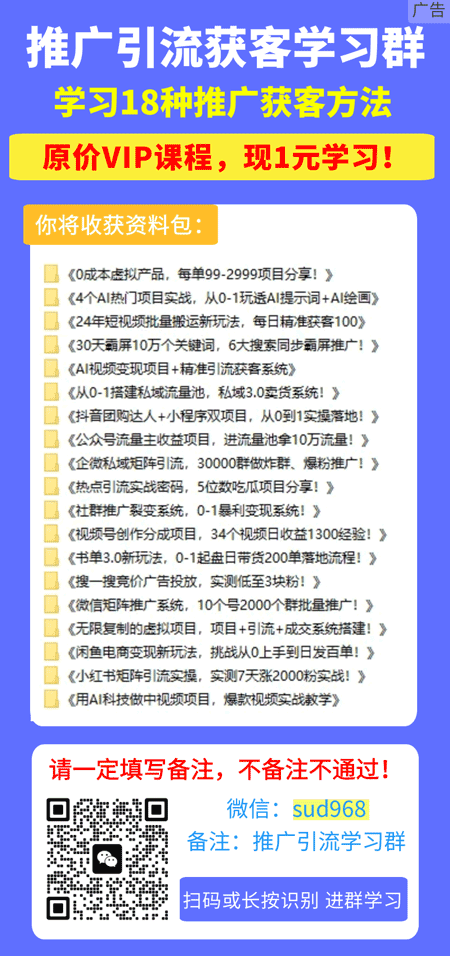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ummeng.com/131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