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寄宿在苦难之中,
人寄宿在伤痛之中,
我倒宁愿在。
—— 马勒第二交响曲之“复活颂”
1
据说《人生大事》最初的名字叫《上》
“天堂”一词在西方,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天堂对灵魂的接纳是有条件的,要忏悔,要赎罪,要历尽苦难。
无论是但丁还是马勒,作品都是自地狱始,至升天终,笼罩着一层崇高的圣光。
在汉语语境下,尽管早期佛教经典中也出现过“天堂”一词,但其早已去宗教化,变成了美好世界的代称,充满了世俗的色彩。
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天堂、转生这些事呢?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一种对还活着的人的安慰罢了。
高亢的唢呐和歇斯底里的哭喊构成一种怪诞的仪式感,悲痛欲绝者在仪式中释放悲痛,怀抱遗憾者在仪式中抚平遗憾,心有亏欠者通过仪式将亏欠自洽。
逝者上了天堂,好了,他的故事已经结束,而我们还要继续排演自己的剧本,继续摸索活着的意义。
中国人对生死话题多少是有些避讳的,不喜欢“4”这个数字,电影中婚庆店的老板一直忌讳隔壁是寿衣店,孩子碰了店里的东西要马上洗手。
也正因此,《人生大事》以中式丧葬文化作为切入点显得新奇又可贵。
“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很多时候被误读为孔子回避死亡,我倒不以为然。活得太过轻盈浅薄的人,是很难谈论死亡的。
如此看来,二手玫瑰创作的宣传曲与本片过分搭调,名为《上天堂》,却句句都在讲怎么活着。
用力活着,是直面死亡的前提。与生活的残酷面近身肉搏后,还能满身带伤地拥抱善与爱,才能把“追名逐利云散场,人生除死无大事”唱得掷地有声。

2
电影中的主角,一个人近中年,一事无成,靠死人赚钱,对死亡早已麻木,活着也如行尸走肉。另一个则尚处在肉体和生命都还在建构的年纪,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与肉体崩坏的过程。
一大一小,一个可悲,一个可怜,凑在一起抱团取暖,逐渐成为彼此依存的力量。
男主角莫三妹对生命的态度,经历了从旁观到介入,再到主导的过程。
片子伊始,他在医院的病房外静静地等待生命消逝,然后找机会说几句漂亮话,拉上一单生意。
被家属骂了也无所谓,换个时间,重新包装下谎言,继续硬着头皮上前。
他对这份工作没有敬意与热爱,只是拿到父亲房产前的权宜之计罢了。
前女友的突然来访成为一个转折点。无法狠下心拒绝为情敌整理仪容的请求,于是不得已求助父亲。
在父亲的指导下,以双手拼合遗体的筋脉骨骼、血肉肌理,努力复原逝者在亲人心中的记忆。
当情敌的面孔重新出现在眼前时,大功告成的释然令他放下了情感的伤痛,并第一次试图思考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
得知哥哥的死因则让这份思考终于有了沉淀。哥哥是在打捞长江中的尸体时淹死的。
为了一个死人,折了一个活人,看上去不值。但所谓一个行业的“圣心”,就是从不计较值得与否。
至此,莫三妹叫停了搬家,重新装修了门脸,带着哥哥与父亲的遗志继续经营下去。
如果说殡葬服务让莫三妹重新整理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孤儿武小文的出现则让他重新拾起了自己与他者的关系。
对于在底层打滚的loser来说,物质援助只能解一时之急,“被需要”的感觉才能真正将他拉出泥淖。
因为被需要,意识到自己还有价值;因为被依恋,身体中得以生长出力量。我们都是在他人的需要和依恋中,愈发活出个人样。
我很喜欢影片中一个细节,起初那把木头制作的红缨枪一直被小文拿在手上,被她当作壮胆和自卫的武器。
后半段建立了如父如女的关系后,红缨枪背在了莫三妹的肩上,象征着爱与信任的给予,仿佛小动物向人露出了柔软的肚皮。

3
尉任之在《室内静物,窗外风景》中写过:“电影是他者经验的压缩。
如果人的成长是学习如何面对亲人、朋友以及他日自己的死亡。那么在看电影的过程里,在最低的限度上,我们借由他者的经验,得到揣摩的机会,认识‘生命有限’这个事实的同时,学习用虔敬之心来遥望这个纷扰的世界。”
人归根结底是社会动物,我们终究还是要靠人与人的联结,来确认自己还活着。这联结是指情感灵魂层面的,而非血缘的。
影片中除了小文和外婆的感情,创作者几乎毫不掩饰对人类血缘关系的失望。
主角在父亲的专制下成长,父子关系一度令人窒息。
小文被生母抛弃,又被舅舅舅妈视为累赘。
那个花30万给自己办葬礼的老人,自从拿到拆迁款后,家中便没了安宁,子孙后代为争遗产闹得不可开交。
电影中那些最温暖的情感,几乎全部来自于没有血缘的陌生人。
明明是宇宙间的随机照面,却碰撞出强烈的火花,灿如星光。
莫三妹告诉小文,人被烧成灰后,会飘到天上,变成星星。小文深夜坐在门前,循环播放着电话手表里外婆的语音,头顶上是一片璀璨的星空。
其实如今的城市里,已经极难看见星星了。这片虚构的天空,是一种浪漫化的表达,比喻着情感的浓度。
那些我们记挂的人们,无处不在,仿佛明亮的星星,永恒骚动着生者的心灵深处。

4
读初中时,我失去了我的祖父。
入殓那天,我内心平静得像刚刚退了潮的大海。仿佛他并未离世,只是像往常一样出门遛弯,过一会就会回来。
直到很多年后,我从国外旅行回来时偶遇一位神貌相似的老人,眼泪突然决堤,悲伤翻滚而来,我在时差的昏聩中追忆逝者,完成了这场迟到多年的告别。
电影中我最喜欢的片段是莫三妹将父亲的骨灰装在烟花中,点燃,升空,盛放。烟火与星光交叠,无比绚烂,构成了短暂生命的绝佳隐喻。
或许,缅怀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思念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上,记住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在没有边界的时空中,在浩渺的宇宙中,赋予他一个坐标。
这样的仪式未必豁达,但似乎到了最后,生命的铅华已经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被淘洗干净了。
是的,天堂之门已经打开,愿所有逝者安息。
文/李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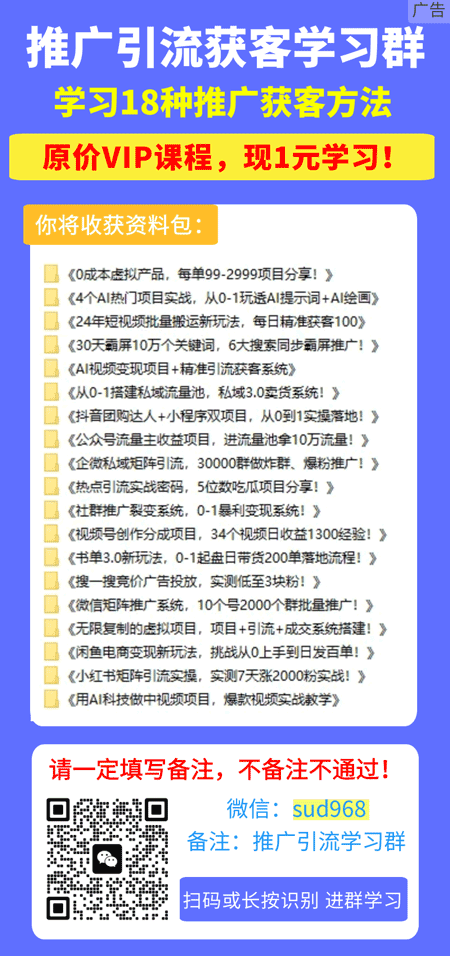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ummeng.com/41505.html